张枣:在新诗中寻觅现代性的言说方式 | 书评
严格来说,张枣的留德博士论文《现代性的追寻: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》有颇多可商榷之处,譬如各章节采取的研究方式不一,对“现代性”缺乏提纲挈领式的表述等。
但瑕不掩瑜,张枣贯穿全书的文本细读无疑是一把钥匙,使通往文本内部之门向缺乏解读手段的读者敞开。从鲁迅到闻一多,从冯至到北岛,张枣从当代诗人的写作经验出发,为我们构筑了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发展脉络。
撰文丨张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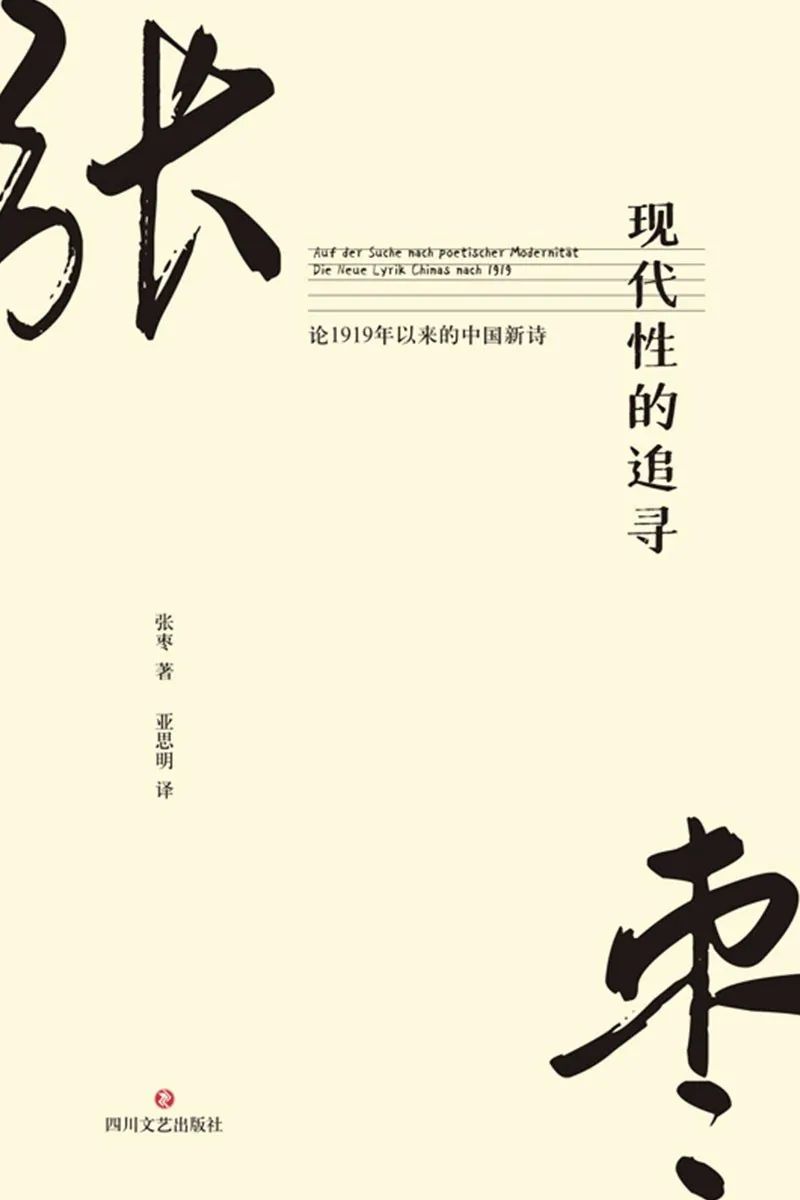
《现代性的追寻: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》
作者:张枣
译者:亚思明
版本: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0年8月
01
何为现代性:无从歌颂,亦无可反叛
何为“现代性”?在谈论这本《现代性的追寻: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》时,有必要先对这个指涉庞杂的词语稍作阐述。
工业革命与全球化塑造了我们现代生活的基本样貌,启蒙运动则定义了现代价值,从这层意义上看,作为一种客观描述的“现代性”以及作为某种价值取向的“现代性”都是社会运动的结果。而在文学意义,尤其是诗歌意义上,“现代性”是结果的再结果。诗人们承受了现代生活(相对于过去时代)的混乱与无力感,亦对过往的精神传统有所反思,从而发展出了现代性的言说方式。
胡戈·弗里德里希在《现代诗歌的结构: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》一书中所言可资借鉴:“诗人们历来就明白,忧愁只有在歌吟中才会冰释。这便是通过将痛苦转化为高度形式化的语言而使痛苦净化的识见。但是直到19世纪,当有目的的受苦转化为了无目的的受苦,转化为了荒芜,最终转化为了虚无时,形式才如此突出地成为了拯救……正如诗歌要与心灵相分离,形式也与内容相分离了。”

《现代性的追寻: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》,[德]胡戈·弗里德里希著, 李双志译,译林出版社,2010年10月。
从“无目的”到“荒芜”乃至“虚无”的递进切中了现代性的核心。在新的现实中,诗人无从歌颂,也无可反叛,意义开始被怀疑并逐渐消解。然而也正在这时,形式的重要性却愈发凸显,甚至脱离整体的主题目的拥有其独立性。亦即是说,一个句子、一种结构可能和整个篇章拥有同等分量。
于是,写作这一历时久远的行为开始被重新认识,它未被重视的功能恰在此时得以凸显。如果言说无力纠正现实,那么,也许它依赖自身的审美功能,能对现实作出对抗甚至超越。这本《现代性的追寻: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》,即是为张枣所辨识出的,汉语诗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循此探索的一条伏线。
02
《野草》:“追寻”自鲁迅始
以往新诗论著多取胡适《白话诗八首》或《尝试集》为起点,强调其作为白话诗源头的文体意义,张枣则不然。在对1949年以前的诗人略作划分后,他选择了鲁迅的《野草》作为阐释的开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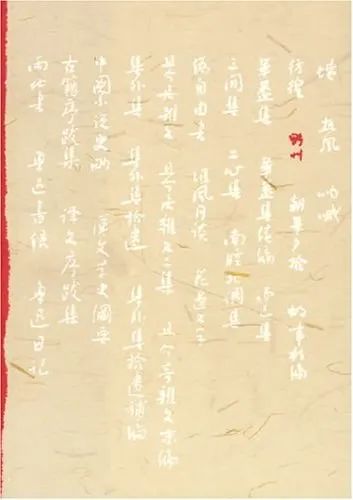
《野草》,鲁迅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6年12月。
从这一选择中,我们更能理解作为一种诗学主张的“现代性”和时序上的“现代”之间的区别。白话文写作固然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,但其背景(或者说,它所寄身的那种实践)却与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不同。汉语诗人何时真正面临现代性语境有待商榷,但大抵是近四十年的事,而1949年以前的汉语诗人,其现代性或者更多依赖于个体禀赋而非整体语境。
在此意义上,张枣对鲁迅的推重是一次诗学意义上的重估,书中对《野草》大篇幅的文本细读,着重强调鲁迅的“元诗”意义,即:将现实中的失语危机再现于言说过程,借象征手法以生发诗意,从而完成精神意义上的自我修复。这意味着,写者并非先在现实中克服危机而后才能结束失语,恰恰相反,言说本身便能对抗甚至超越现实。而且,借非个人化的写者自觉,对抗与超越亦非自我耽溺。
譬如《秋夜》一篇,“我”仅作为一个默然的观察者存在,而在视域中,“冷眼”“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的天空”构成一种压制力量,落尽叶子的枣树却有最直最长的几枝直刺天空——这是一组对峙,但对峙之外却仍有冷夜中瑟缩,却依然梦见春天的小花以及扑向灯罩的苍翠的可爱、可怜的小飞虫。
值得注意的是,在《秋夜》中,叙述天空和枣树的,均为冷静平抑的语气,但谈到小花和飞虫时,却使用了极为细密怜惜的音调。这无疑是宣称,其文心在此而不在彼。同样的,作为一种写作姿态的再现,诗意生发的动作亦在此而不在彼。
《野草》中的二十余篇,大多类于此种情境。当然,言说者未必每次都能寻到慰藉,有时也彷徨茫然。但确定的是,他并非置身对抗,而是潜心寻觅,和《野草》以外的文本不同,亦和鲁迅为人们所熟知的那个峻刻形象不同。盖因这并非对峙的时刻,而是努力克服失语,自我修复的时刻。
不过,张枣对鲁迅的观察固然带来了重新认识《野草》的可能。然而,鲁迅究竟抱有多大程度的现代性自觉依然值得商榷,这并非对文本自身的不满,而是对生成《野草》的处境存有排斥心。换言之,鲁迅先知先觉地辨认出了可能的现代性语境,却对此心存抵牾。故而他在《野草·题辞》中说道:
我自爱我的野草,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。
……
我以这一丛野草,在明与暗,生与死,过去与未来之际,献于友与仇,人与兽,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。为我自己,为友与仇,人与兽,爱者与不爱者,我希望这野草的朽腐,火速到来。要不然,我先就未曾生存,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。
03
诗人的冒险:在两难中寻觅
除了对鲁迅的重估外,这本书揭示的另一个重要主题,是追寻者身上的两难困境。
现代主义生成于浪漫主义之后,它对浪漫主义的警惕,在“去个人化”这一点上体现的十分明确,不谋求诗人个体强烈情感的显现,亦避免一种单调的强音(譬如雪莱在《西风颂》中那种强烈的吁请语气)。诗人作为抒情主体,往往自我简化,或者戴了面具,扮成他者(如马拉美笔下的牧神)。其意识亦通过象征的手法投射到外物上。
如此一来,当抒情主体与客体都被客观化之后,写作也由一种高度内在的行为转化为一门客观化的技艺。诗意不再由诗人主体性的声音生发,而是在语言自身的秘密中被寻觅。由此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发展出了“纯诗”概念,要求诗歌摒弃日常经验与教化,任语言魔术发挥作用。
从张枣的书中,我们能看到,在鲁迅之后,闻一多、卞之琳等1949年以前的代表性诗人,察觉到了纯诗的写作自觉,并创作出了有启发性的现代性作品。但社会现实却牵动着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,将他们置于纯诗与现实的两难中。
在闻一多的《静夜》中,这种两难最为明显:
这灯光,这灯光漂白了的四壁
这贤良的桌椅,朋友似的亲密
这古书的纸香一阵阵的袭来
……
如果只是为了一杯酒,一本诗,
静夜里钟摆摇来的一片闲适,
就听不见了你们四邻的呻吟,
看不见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,
战壕里的痉挛,疯人咬着病榻,
和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。
这一时段的诗人,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革命实践,客观上造成了现代性探索的断裂。现代性再度被拾起,是在先锋诗人群体中,当诗人们体悟到诗作为一种对抗性语调的可疑后,他们重新打量自己的写者姿态,并回归到对语言的自律中。
这并不等于说,诗人们就能从两难中抽身。只不过,从一种可辨认的特殊困境,转向了更具普遍意义的现代性困境。
在他早于本书的《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》一文中,张枣曾断言,当代先锋诗歌所面临的危机是先锋诗歌在追寻元诗结构的过程中,对“词即是物”这一信念的实践,最终背离汉语诗歌“词不是物,诗歌必须改变自己和生活”的美学信念,从而呼吁在先锋诗歌的发展中包孕这一两难处境而继续向前。他本人也曾以“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,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、正派和大度。只有这样,我们的语言才能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、纠葛、表情和饮食起居”声明自身的写者姿态以及对汉语传统的维护。
但在本书中,张枣却只引用了《朝向》第二节对先锋诗歌的文本细读,并从荷尔德林的“敞开领域”中另辟新论,要求写者向“敞开而无可能”的远方冒险。实际上,这仍然要求诗容纳生活,并为荷尔德林所言“诗意的栖居”敞开一整个大地。只不过,现代生活急剧变化带来的陌生感,使得“大地”生成之前,诗人们首先要向那光怪陆离的远方,展开恒久的冒险。
















